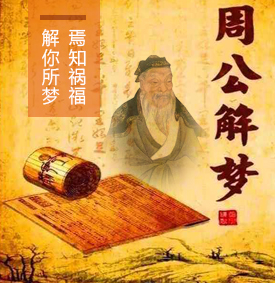发布时间:2015-11-07 11:07:53
发布人:
派拉
在清理家母遗稿时,从家母电脑中,看到这篇翻译出的文章。说实话,我真不知家母定稿没。现无法,也不可能再问,只有当成付梓稿来阅读了。扑索迷离的故事情节、优美流畅的语句深深吸引着我,一气读完后仍意犹未尽。对家母深厚的中英文文学及翻译功底,钦佩不已,为有这样的母亲搞到自豪和骄傲。
这篇泰戈尔所著《在加尔各答路上》,是家母按照原版书籍翻译成的。在翻译过程中她力求忠实于原著,包括文章和其中的人物对话。严格遵照原文的习惯和语法、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国人的讲话习惯及语法。在可读性、趣味性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,使其通俗易懂耐人寻味。
通篇文章语句优美,用词得当,如一股清泉在文字间流淌。好的翻译作品,能让读者感觉到与作者对话,这座心灵桥梁的建造者就是翻译工作者。《在加尔各答路上》是篇国内难得、少有的好译本,值得借鉴和阅读。现将这篇翻译文章,全文转载如下:
我到大吉岭(1)的时候,碰到那里阴沉多雾——是一种使人懒得出门而呆在屋里更不自在的天气。我在旅社用过早点,穿上大皮靴子,大衣,走了出去,做我的例行散步。
细雨一阵阵飘拂,云雾笼罩群山,蒙蒙一片,把山景幻画成一幅是画师涂抹过的画面。我沿着加尔各答公路悠然独步,突然听到附近有女人呜咽的声音。当然,在别的时候,我也许不会注意;但在这无边迷雾之中,它却哀怨如诉,如同窒息的世界也在哽咽,不容你不去倾听。
走到那个地点,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路边石头上。她的头发,被太阳晒成青铜色,乱蓬蓬的一片,盘在头上;而那一声声,从她心灵深处发出的哀恸就像是什么抑郁已久,绝望的苦痛,在这云雾弥漫,凄凉寂寞的荒山野麓,全部倾泻出来的。
我用印第语(2)问她是什么人,为什么哭。起初她没有应声,只隔着雾气,含泪对我瞧着。我叫她不要害怕。
她苦笑一下,用道地的印度斯坦语(3)回答我说:“我早就无所畏惧了;甚至连羞耻也都丧失。可是,先生呀,从前有一段时候,当我住在自己的宫闱里,就是我兄弟也得预先请见才能进来。而如今,茫茫大地之上,我连帏幔都没有留下一条。”
“你要不要我帮助?”我问。她沉着地注视着我的脸回答:“我本来是巴德朗(4)大君,瓜拉姆·揆德尔可汗的女儿呢。”
巴德朗在什么地方,世界上不管是谁在那里称孤边寡,多少咄咄怪事之中偏偏是她的女儿变成这样一个苦行者,在加尔各答路上一一方角落里嚎啕痛哭——这一些我既想像不出,也不能够相信。不过,回头一想,我又何必过于追究;这种说法不也耐人寻味?因此,我严肃地按照正规礼节,深深行了一个额手礼,道歉说:“请原谅,公主殿下,我没有料到你是殿下。”
这位公主显然喜欢奉承,她招呼我在附近一块石头上坐下,摆一下手说:“请坐。”
从她举止之中,我发现她的风度高雅自然,有一种能指使人的威严,不过,要我坐在她身旁那块坚硬、潮湿、布漫苔藓的石头上实在不是一个叫人领情的恩赐。那天早上,披上大衣踱出旅舍,我万想不到竟会如此受宠若惊地,坐在巴德朗的瓜拉姆·揆德尔可汗女儿玉体旁的,一块泥泞石头上。她的芳名也许是什么“帝国之光”或“宇宙之光”。
我问她:“公主殿下,什么事情会使您落到这步田地呢?”
公主用手摸了一下额角说:“我怎么能够说是谁把我弄成这样呢?——你能告诉我是谁把这座山流放到云烟深处来的?”
当时,我并不想卷入哲学奇论,因而只顺着她的语气说:“是的,殿下,您说的对。谁能探索命运的奥密呢?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人。”
其它场合,我也许会和她争论,把论点说清楚,但我对印度斯坦语一无所知,这种情况阻止了我。我那一点零星从工人那里学来的印弟语,在大吉岭这条山阴道上,不论是和巴德朗公主或其它任何人,当然不能助我把什么命运以及自由意志一类问题阐述清楚。
公主说:“我一生奇迹一般的恋爱故事,刚刚就在今天,彻底破灭了。如果你许可,我可以完全讲给你听。”
我连忙接上她的话头。“许可——听您讲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呢!”
了解我的人会理解,以我的话说来,我欣赏印度斯坦语流畅自如,胜过它的语法规范。换句话,公主和我讲话,她的词句就像清晨和风,在金光闪闪的麦田上飘拂。以她而言,她的话语流畅、文雅,来得极其自然;而我的对答却是简短,不成章句的。
她的故事是这样:
“我父亲脉管里流动着的是德里的高贵血统,因此为我选一个门当户对的驸马很不容易。有人建议把我许给勤克脑(5)大君,而我父亲也在犹豫;正在这时,印度士兵反抗巴哈杜尔连队的大起义(6)爆发,印度斯坦被人民的热血染红,又被大炮的硝烟熏成焦土。”
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听过印度斯坦语,这样优美地从一个妇女嘴里讲出来。我只能体会:它是一种封建王室的语言,不适合现代贸易频繁的机械时代。她声音里有种毅力,恰恰在英国山卡的中心地带,在我眼面前召唤出来了:一些高入云霄的白大理石,蒙古式宫殿的圆顶穹窿,披着漂亮马衣,曳着尾裙的骏马,安着豪华宝座和华盖的大象,缠着五光十色的包头,佩着弯刀的华美肩带,穿着脚尖翘起来的绣金鞋子,披着潇洒而飘飘然的丝绸,或细纱长袍的朝臣,以及一系列浩浩荡荡,随之而来的宫庭仪式。
公主继续讲她的故事:
“我们的城堡在乔姆河河岸,由一个印度婆罗门(7),凯雪夫·拉尔守护——”一提凯雪夫·拉尔这个名字,这个女人仿佛一下子把她声音里的美妙音调都倾吐出来了。我的手杖落到地上,我直楞楞坐地那里,急切地听着。
“凯雪夫·拉尔”,她接着说,“是一个奉正教的印度人。每天拂晓,我从我闺房窗格子里面都可以看见他,那时他总是站在水齐胸口的乔姆纳河水里,把他的奠水献给太阳神。他还在河畔大理石台阶上打坐,长裙拂地,默默背诵经文,后来又以他清澈动听的声音唱着赞美诗回家。”
“我原是一个信奉伊斯兰的女孩;不过我从没有得到机会研究我自己的宗教,也没有做任何拜祷的习惯。我们的人,那些时候,早都成了散漫没有信仰的了。而我的宫院,放弃了宗教信仰,只不过是一些游乐场所。因此,不知怎地,我却自然而然地渴望着精神慰藉。当我在晨光熹微之中,亲眼看到那一幅虔诚的图景,低处,白色石级一步步通往乔姆纳河,静幽幽的碧波,我才醒觉过来的心灵也泛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,皈依神灵的温馨感觉。”
“我有一个印度女奴。她每天清晨总去给凯雪夫·拉尔擦洗脚上的灰尘。这种礼式常常引起了我的兴趣,同时又是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点忌妒的原因。喜庆吉日这个女孩子还供奉婆罗门,给他们呈献祭礼。我常常赏她钱,帮助她这样做。有一次还要她请凯雪夫·拉尔到她家去宴饮庆祝,不料,她居然傲慢起来,还说她们教主凯雪夫·拉尔从来不接收任何人的酒宴或敬奉的。这样,我无论直接或间接,都无从向凯雪夫·拉尔表达我的敬意;我内心就更是如饥如渴地向往着他。我有一位祖先曾经把一个婆罗门姑娘强霸地,抢到自己内苑。我时常想我自己脉搏里大概也有她的血液在颤动。这种想法常常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满足,觉得凯雪夫·拉尔和我还有些亲眷关系。我的印度女奴从许多历史诗篇详细朗诵的一些男女爱神的离奇事迹,我都听得津津有味;在我心里也建立了一个印度教化至高无上的理想世界。神的形象,寺钟和法螺的音响,庙宇上的金顶,缭绕着烟香,鲜花供果和檀香木的芬芳,瑜珈(8)的无边法力,婆罗门的尊严,渎神叛动贬为凡人的种种传闻——这一切充满了我的幻觉,缔造了一个广大而飘渺的理想王国。我的心在这一片仙境里飞翔,如同一个在暮色中穿房夺户的小鸟,腾飞在一栋宽敞的古老大厦里”。
“之后大起义爆发,我们在巴德朗的小小城堡也感到它的震撼。印度教、伊斯兰教为了印度斯坦王位,自古以来从未休止的争夺战,再一次孤注一掷的时候到了;残杀耕牛的白人屠夫,也该从雅利安国(9)土驱逐出境了。”
“我父亲,瓜拉姆,揆德尔可汗是一个工于心术的人。他痛骂英国人,同时也这样说:‘这些人是什么都做得出的,印度人比不过他们。我犯不着为一种徒劳无益的冒险事情,牺牲我的城池,我不打算和巴哈杜尔连队开火。’”
“在印度斯坦,每一个印度教徒和伊期斯兰教徒都是热血沸腾;而父亲在这生死关头,居然提出这种警告,实在令我们大家感到可耻。甚至一些老妃嫔也在焦急。这时候,凯雪夫·拉尔率领他所统率的全体军民,发表了个公开声明:‘大君陛下,假若陛下不和我们站在一起,那么,战争进行期间,我们只能将陛下监护起来,由我来守卫城堡。’”
“我父亲答复说,这样性急没有必要,因为他本人还是准备和起义军敌忾同仇的。但是凯雪夫向国库申请军饷,我父亲只给他一小笔钱,推说必要的时候再增发款项。”
“我取下我所有的饰物——那些从头到脚装饰我的那些贵重物品,叫我的印度女奴偷偷地给凯雪夫·拉尔送去。他接受了之后,我的这些肢体,脱去了一切装饰,也为此感到兴奋。他开始备战,开始去擦刷那些旧式枪枝和久未动用的刀剑锈渍。可是一天下午,英国总督突然率领他的白鬼子红衣军,开到城堡。我父亲,瓜拉姆·揆德尔可汗私下把凯雪夫·拉尔的秘密计划向他告密了。即使这样,这一个婆罗门的威信这样高,还能使他的小队随从,照样拿起破枪锈剑,出来应战。我觉得我为了这一次奇耻大辱心都醉了,而我没有流泪。”
“我偷偷从我的后宫溜出,穿上我兄弟的衣服,化了装。战争的硝烟,战士的呐喊,枪炮的轰鸣都平静了。人间,天上都笼罩在一片可怕的死的沉寂里。太阳染红了乔姆纳河的碧波,也浑身血迹地落下休息去了;月亮,将圆没圆的月亮,在暮霭中露出凄清的寒光;战场上布满了死亡和痛苦的恐怖景像。。。别的时候要我在这样一种景像之中走过,简直是不可能事。然而,那天晚间上,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梦游人,唯一的希望是寻找凯雪夫·拉尔,其它一切都置之度外了。
“我梦游到午夜,才在乔姆纳河附近芒果树丛里找到了凯雪夫·拉尔。他和他的忠实仆人,在他身边的德奥齐的尸体一起倒在地上。我确信,不是他受了致命伤,义仆把他带到这里;就是这个伤势严重的主人,把他的义仆弄到这个安全处所来的。我长期以来秘密加深的敬慕心情,这时再也抑制不住了。我扑到凯雪夫·拉尔脚边,打散了我的头发,用我的缕缕青丝去擦洗他脚上的泥垢;用额角去接触他的双脚,我的被禁锢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“正在这个时候,凯雪夫·拉尔动了一下,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。他的双眼紧闭,但我听见他在虚弱地要求喝水。我立刻跑到乔姆纳河边,把衣襟浸在水里,把水拧到他半开半闭的嘴唇里,我扯破了我的一块衣服,包住了他的左眼,这里挨过一刀,深深的一条伤痕一直划到头皮。我拧水喂了他几回,在他脸上也洒了几次水,他才渐渐恢复了知觉。我问他还要不要水喝,他却盯着眼睛看我,问我是谁。我再也不能自持,回答他说,‘我是您忠实的奴婢,瓜拉姆,揆德尔可汗的女儿’。”
我心里怀着这样希望,想凯雪夫·拉尔临终把我最后的表白带去。没有人能剥夺我这一次最终的幸福了。但他一听到我的名字,叫了起来:‘叛徒的女儿,背信弃义的!在我临终的时候,你简直把我的一生都亵渎(10)了!——骂到这些字眼,他还对我右脸狠命的打了一击。我感觉一阵昏弦,眼前的一切都黑暗了。
“你要知道,发生这件事的时候,我只有十六岁。平生我是第一次走出宫门,户外炎酷的天光,还未夺去我娇嫩的容颜。然而,恰恰在这出走的第一遭,我竟从我内心世界所供奉的神明那里,得到这样一种问讯!”
我像一个消失于梦境的人,迷惘地听着这位苦行人的陈述,我甚至于没有注意我的香烟已经熄灭了。我的心到底是被印地语优美的音颤,是被她婉转如歌的声音,还是被这个动人的故事吸引住了。这是很难说的,但我一直默默地听着。不过,听她讲到这里,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,不禁喊了一声:“畜生!”
大君的女儿说:“谁是畜生!难道畜生在垂死挣扎时会舍弃在捧到他嘴边的一掏清水?”
我立刻改正自己说:“啊,是的!这是神圣不可侵犯!”
可是大君的女儿又说:“神圣?你是打算告诉我,神圣不可侵犯的人,会摈弃一颗赤诚心奉献于他的深深敬意?”
这样一来,我想最好是不开口为妙,大君的女儿继续讲:
“起初一刹那,这一击耳光对我简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。我的破灭了的世界仿佛都倒塌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倒退几步,重新向那一个狠心、残忍,不可冒犯的婆罗门战士顶礼(11),心里默默念着:‘你从来不要贱者为你服务,不接受异族的馈敬,富人的钱财,不理会年青人的春青,妇女的爱!您是超凡的,远超世俗,——在一切红尘污垢之上的。我甚至于没有资格把自己奉献给您!’”
“我不知道当他看见我,这一个大君宠惯了的女儿,在向他顶礼,头角触地的时候,他心里有过什么感触。不过,他脸上并没有什么惊奇或其它情感的表情(12)。他对着我的脸看了半天,缓缓站了起来。”
“我连忙伸手去扶他,可是,他却默黩地地摆开了我,忍着极大的痛苦,把他自己拖到乔姆河渡口。那里有一条船系着,而周围一个过客,一个船夫也没有。凯雪夫·拉尔爬进了船,解开绳缆,随着流水飘到河心,看不见了。”
“一霎间,我激动得也想把自己投到乔姆纳河水里去,像一朵过早从枝头攀摘下来的蓓蕾——把我所有的青春,情爱和遭到摈弃的敬意,一骨脑都向那一条凌波而去,向载走凯雪夫·拉尔渡船呈献出去。然而,我不能。西偏了的明月,乔姆河对岸深幽幽的一带平林,恬静舒展开去的深深碧波,远处芒果树丛上面,微微闪光的,我们的城堡——每一样东西都在对我唱着无声的挽歌。只有那一条被流水带到没有希望遥远地方去的,摇晃不稳的小小渡船,把我从这一片宁静月夜,美丽的死亡怀抱里拉了回来,指使我向生的大路上走去。”
“我如同一个失魂落魄的人,沿着乔姆纳河岸向前踯躅着,过了芦苇密集,荒芜的沙洲,有时跋涉浅水,有时攀援峭壁,有时又在灌木丛生的草原上兜转。”
她在这里停了,我没有打断她的深思,隔了许久她才重新讲了下去。
“从此以后,事情变复杂了,我不知道怎样一件件地提,把我的事情说清楚。人仿佛是一个寻路于蛮荒的人,盲然摸不清方向。我的长期流浪,究竟经过了多少杳无人迹的险蔽处所,实在难以一一回忆。从哪里说起,怎么收尾,保留什么,删掉什么,怎么样讲清楚,才不叫你觉得莫名其妙呢?不过,多年艰苦的生涯告诉我: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,更没有绝对的困难。对于一个在大君内苑娇生惯养的少女说来,起初,困难的确是难以克服;而这不过是想当然而已。走到群众中间,你总会找到什么出路。这种路也许不是一个大君的路,但它总是一条把人引到不同命运里去的道路——一条崎岖不平,万转千回,永无止境的路,一条充满欢乐,忧患,或障碍重重的道路——永远是一条路。”
“我沿着一条普通老百姓的道路,四处流荡。许多遭遇并不动听,即使动听,我也没有气力详细述说了。总之,我历尽忧患、危险和凌辱——而生活还不是不可忍爱的。我像一支火箭,越燃烧,越飞得高。只要我保持着这种高速的动力,我就不会感到燃烧的痛苦;但当我最大的幸福,和最深的痛苦的热火,熄灭之后,我只得精疲力竭地落到尘埃上。我的高飞远举,就在今天到达终点。我的故事也从此了结。”她停止了。
但我摇了摇头,自言自语:这不算是真正的结局呀,于是,我用不完全的印地语对她说:“殿下,假若是我失礼,请求您原谅我。不过,我相信,要是您能把事情结局再说清楚一点,就能把我的疑团解开了。”
大君的女儿微微一笑。我发觉我这点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居然还有一点效果。假若我说的是道地的印度斯坦语,她也许不能够克服她的反感的;想不到我的词不达意还能起这样的感应作用。她继续说:——
“我时时刻时听到凯雪夫·拉尔的消息,可是我总没有机会见到他。他加入了唐西亚·托庇义勇军,像雷电一样急遽闪现,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,一会儿突然消失了。我换上了苦行者装束来到班纳瑞斯(13),去和西凡纳达·斯瓦来学习梵文经典;拜西凡纳达·期瓦来为师父。印度各处的新闻,都要送到他的法庭来的。在我虔诚向他学习时,我常常也焦急地打听战争的消息。英国老爷们在印度斯坦到处横行霸道,把义军暗中燃烧的抵抗余烬,践踏下去了。”
“后来我没有办法打听凯雪夫·拉尔的消息了。远方,地平线上,复仇的红光之中,时而闪耀着的一些形象,忽然都跃进黑暗之中。”
“我离开师父居处,沿门化缘,寻找凯雪夫·拉尔。我到处巡查进礼,始终没有碰见过他。认识他的人说他一定是送了命,不是牺牲在战场上,就是被战后的军法处决了。然而,一个微微的声音在我心里重复着:这不可能。凯雪夫·拉尔不会死。这一个婆罗门,这一个耀眼的火焰不会熄灭。它一定还在什么难以到达的,世人的神龛里燃烧着,等候我的生命和灵魂去做最后的献礼。”
“印度经文之中有许多贱民由于苦修变成婆罗门的例子,不过伊斯兰教是否也能变成婆罗门的问题,却从来没有讨论过。我知道在我和凯雪夫·拉尔会合之前,我一定得长期容忍,因为我必须先变成一个婆罗门才行。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”
“在内心和生活习惯中都变成了一个婆罗门。那脉从我祖先那一代祖妣所延续下来的血统纯化了我的血液,在我的肢体内悸动。我功德圆满之后一定会毫不迟疑地,把我的整个心灵,显献到我少女初期,最初认识的那个婆罗门的脚下——那一位充满了我心宇的婆罗门。那时我就会感觉我头上有光环围绕了。”
“我常常听见人家讲凯雪夫·拉尔骏勇抗敌的事迹,但这些在我心里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我心目中长远闪耀着的是那一幅凯雪夫·拉尔在幽静,映着皎洁月色的乔姆纳河飘往下游的,那个小小渡船的画面。我日日夜夜看见他向一个飘渺无路的神秘处所飘去;没有伴侣,弁去随从。那是一个完全自主,不需要别人的婆罗门。”
“最后,我终于打听到凯雪夫·拉尔的消息。——他逃避刑役已经从印度、尼泊尔边境逃出去了。我也到了尼泊尔。在那里逗留了很久,才知道他几年以前早离开尼泊尔了。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从此,我又从一座山转到另一座山,追寻着他。那些村落不是印度教区,不丹和莱普卡(14)人都是异教徒,他们饮食无度,他们信奉他们自己的神,有他们的信仰方式。因此,我不得不神经过敏地躲避着一切污秽,进行我自己的清规。我知道我的渡船快要进港了,我的世俗生命最终目的也遥遥在望,不太远了。”
“但是,我该怎样把它讲完呢?一切结局都是短暂的。吹熄一盏灯只有猛的一口气就行。对,那么,为什么我还喃喃不已地,说个没完呢?就在今天早晨,在分别了三十八年之后,我又遇见了凯雪夫·拉尔——”
她讲到这里,我又急得忍不住了,便问了一句:“您是怎么看见他的”
大君的女儿回答:“我看见衰老了的凯雪夫·拉尔,在一个不丹人的村子里,在稻场上打麦子。他的不丹老婆在他旁边,他的不丹孙子,孙女围在周围。”
故事在此结束。
我想我应当说点什么——只要几句话——来安慰她。我说:“一个不得不和异族共处三十八年之久,为保留性命而隐逸的人——他怎么能够遵守自己的教规呢?”
大君的女儿回答:
“难道我这也不懂?可是,可是,多少年来,我眷恋不舍的,是怎样一种幻想啊!——在我青春年少,这个窃取我心灵的婆罗门,所加之于我的那种困惑?难道我会怀疑他之奉教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吗?我认为他那样才是道行,真正、永久的道行。不然,我怎么会把那一击耳光当作我教主的教法!——那一次不可容忍的侮辱!——在我十六岁的时候,在我第一次离开有我父亲荫庇着宫院,满怀热情和信心,兢兢业业把我身心和青春向他呈献。。。而这个婆罗门,为了报答我这一切,所给我的那一击!呵!婆罗门!你自己却接受了另外一种,用我所失去的生活,和青春,去换取另外一种生活和青春?”
这样哀叹着。这位苦修的女人站起来说:“再见了,先生。”可是走了一刻,她又改了口气,用伊斯兰教语说了一句同样的话。
改用伊斯兰语致意,她不啻是和她幻灭了的婆罗门理想作了诀别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,她已经在喜马拉雅山路,灰蒙蒙的云雾里消失了。
我把眼睛闭了一会,她所讲的一幕幕又在我心头放映了一次——那一个二八年华,坐在窗格子旁边,波斯毯子上,遥望着婆罗门在乔姆纳河里朝沭的,大君的女儿;那一个披着袈挲在什么灵山法寺,做上灯式晚祷的忧郁女人;那一个肩负河山破碎,理想破灭的沉重痛苦,僵化在大吉岭加尔答路上的孤苦身影。那个汇合两种血液的女人的凄凉音调,仍然在我心头回响。她那一种混合语言的语调尤其是优美而绝对高贵的。
很久我才把眼睛睁开了,雾已经消散,山坡上晨曦耀目,英国女人坐人力车出来兜风;英国男士都有骑着马。一个孟加拉人(15)办事员,头缩在围巾里面,不时从围巾的皱褶里,好奇地,偷偷打量着我。
加尔各答路街景
注:
(1)印度地名,在印度喜马拉雅山麓。是印度交通要道和避暑盛地。
(2)北印度语,采用梵大字母,写的时候从左到右,泰戈尔的孟加拉语和它相近。
(3)印度伊斯兰教徒的语言,用的是阿拉伯字母,写时从右到左。
(4)印度北部旧时的封建领邦,在恒河支流乔姆纳河流域。
(5)印度北部旧时的封建领邦,在恒河上游,现在是印度的弟四方城市。
(6)当时印度受英国压迫已久,各阶层革命热情高涨。1857看德里附近密鱼特士兵首先发动杀死英国军官,德里士兵立即响应,各地同起支援,号召消除宗教成见。团结起来,打倒英殖民者。
(7)印度僧侣集团,后来爬上统治集团最高位置。婆罗门教分人民为四等。只有他们有反侍奉神。并监督执法。
(8)瑜珞——印度哲学的一派,主张默坐沉思,刻苦修行,追求超出自然的伟大力量。
(9)纪元前2000年左右,雅利安人从西化侵入印度征服土番达毗茶人,建立了许多奴隶制的小国。
(10)作为高级婆罗门,喝伊斯兰教徒手里送来的水,即使是下意识地,也是莫大屈辱。
(11)英帝国主义当时在印度制造分裂,煸动宗教仇恨,而泰戈女主角却愿用爱和信仰感化对方。
(12)婆罗门法师浸礼时一向不动声色,不管信使如何谦卑,供礼如何贵重。
(13)印度圣城,在恒河西岸,城里有宙宇和伊斯兰教堂1700所,是著名印度教布道场所。东南离加尔答450里,水陆交通都很方便。
(14)不丹西面小国——西金(哲孟雄)的一种民族。
(15)印度省名,省府是加尔各达。不是孟加拉果。
范亚维 译
罗宾德让纳斯·泰戈尔(1861-1941),印度近代伟大的爱国文学家,1913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,是我国人民最熟知的作家。由于过去中国和印度同样遭受殖民主义者的相互残酷迫害,所以他对我国深表同情。1881年距今一百年前,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,他就曾著文谴责英帝国主义在我国倾销鸦片的罪行,1924年访问我国之后又多次发表文章,支持我国反帝斗争,1938年逾以七十七高龄,为日军侵略我国种种野蛮行经写公开信给日本,印度人尊劳他为“印度的良知”。
泰戈尔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,他的小说往往也像诗一般瑰丽。本篇以抒情笔调描写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个侧面,篇中提到的两种宗教的鸿沟是印度民族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,女主角为参加义军,弃家出走,力求消除宗教分歧,而结局河山破碎,理想破灭,具中涵义更是耐人寻味.
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>>